故乡的草鞋(散文)
文/代应坤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载满舱/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充满希望的启航......”,每当听到张明敏《爸爸的草鞋》这首歌,我的思绪便张开翅膀,飞到那难以忘怀的40多年前。
我家住在安徽寿县西南角一个偏僻而美丽的村庄,一条上连淠河、下入淮河的无名河,常年流淌着清澈照人的山泉水,河的两岸是婀娜的柳树,青青的草。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除了放猪牧羊,便是逮鱼摸虾,要想不光着脚板,就只有跟草鞋亲近了。
记忆中的草鞋,朴实,敦厚,亲切,在农家人心目中的份量,丝毫不逊于今天的皮鞋。淡黄色散发着泥土气息的草鞋,或薄,或厚,薄的夏秋季节穿,厚的冬春季节穿,那是父亲做完农活回家以后,煤油灯下用一根一根的稻草编制出来的,暗淡的灯光下,父亲核桃一般的脸上挂满沉思和满足,那是一天只吃两顿饭,大年三十都不歇工的时代,所有当家主的共同表情。刚编制好的草鞋,一开始穿在脚上极不舒服,像一个无形的嘴巴,撕咬着我和两个妹妹稚嫩的脚面、脚掌、脚心,血泡是必然的,但很快我们就会忘记,因为相比那些光着脚板走路的孩子,我们算是幸运的,秋雨中的颤栗,夏阳下的烤脚,我从来没有体会过。
草鞋的地位比较突出,它与锄头、镰刀、庄稼和田野紧紧地连在一起。东方地平线一轮红日升起,随着一声哨子响,生产队队长就吆喝上工,于是,父亲走,母亲走,草鞋也走,一起去田间耕种劳作,在主人一左一右、一起一落的动作里沾满上了泥土和露珠的气息;西天边落下最后一抹夕阳的时候,草鞋浑身上下都充满着一种岁月安好的味道,披着淡淡的晚霞,随林间的清风与主人踏歌归来,此后便被置于土墙的一侧,在疲倦和知足中想着心事,在月光的沐浴下静静入眠,等待着新一轮周而复始的出行……
刻在记忆深处的草鞋故事,与那个飘飘洒洒的飞雪之日有关。
一夜西北风,带着哨音,第二天一早醒来,门前堆满了几尺深的雪。我穿着厚厚的足有半斤重的草鞋,艰难地行走着,摔趴下,再爬起,一路上就这样反复着。家离学校五里地呢,多是羊肠小道,还有几处小沟和水渠,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河岸的杨柳和槐树,在飞雪中看上去影影绰绰的,天与地显得如此的苍茫,又如此地亲近。走着走着,一颗泪珠不听话地悄然滚落,怕是要迟到了,迟到要挨训的。
我终究还是迟到了,但老师没有训我,坐在座位上,眼睛盯着黑板,心却在自己的脚下,草鞋内灌满了雪,冰水噬咬着我的双脚。
1978年以后,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草鞋渐渐被布鞋和胶靴替代,乡下人除了吃饭问题被解决,生产出来的多余粮食也走向街头,换成现钱,买布匹自己做鞋,或者买球鞋,买胶鞋,都成为可能。
1981年夏,我考取了一所中专学校,意味着跳出农门,捧起了铁饭碗。临上学的前一天,父亲卖了几袋油菜籽,又借了十块钱,给我买了一双黑色的皮鞋,父亲先把脚伸进鞋内试了试,说了声“舒坦!”,核桃般的脸上立即开满了花朵。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我脚上开始套着各种颜色、各种式样、各种价位的皮鞋,但是,我心底的草鞋情结还原封不动地趴在那儿,随时打开,还是光亮如初。
草鞋慢慢活成了一种记忆,活成了对峥嵘岁月的追思。原本跟镰刀、锄头平起平坐的草鞋,在岁月的大浪淘沙中,最先没有了它的踪影。见不到草鞋,只能从古诗词中寻找心灵的寄托:黄庭坚《渔家傲》“踏破草鞋参到了,等闲拾得衣中宝。”范成大《催租行》“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 伊用昌《题茶陵县门》“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字里行间,草鞋被赋予生命的意义,有了一种敦实的风骨,在历史风尘处静默生香。
这些年来,故乡的人外出了一茬又一茬,只留有部分上了年纪的老人守着青瓦、老街、独院过日子,即使踏破铁鞋也找不到当初的草鞋了!当然,我并不伤感,我只是心中充满了怀念,怀念是每一位即将进入老年群体的人的通性,我怀念过去的那一段光阴,那一段物质匮乏却激情燃烧的岁月,草鞋,做为清贫时代的特定之物,成了今天人们不忘过去展望未来的标本性记忆。在满大街摆放着皮鞋、布鞋、运动鞋,老人儿童人均拥有几双鞋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从心底感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尽管前进的道路坎坷不平,但是,国家一直是昂扬向上的,做为一名亲历者,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故事长满天涯海角,包括你和你的故乡。”我们都有过岁月的锤炼,经过风雨的洗刷,这才有了昨天和今天的对比,故乡如此,草鞋也如此。那见证着我们一家几代人成长过程的草鞋,是千里之外的游子丢在故乡的魂魄。(1769字)
通联: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甲69号西山国际城七号楼217室北京市安都律师事务所
邮编:100041 电话:13731949466 13661118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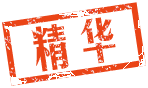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