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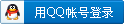
x
在飘尘闪小说研究会上的发言 文/杨轻抒 闪小说目前比较热闹,社会比较欢迎这种短小的体裁;闪小说的作者也感觉比较良好,有点开创了某种路子的感觉。但作为近几年才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闪小说是一个左右不怎么讨好的东西。闪,意思就是文字少,有的只有几十个字,百来字,但这很容易就陷入了段子的陷阱——你说你写的是闪小说,别人直接表扬你这个段子编得还将就,这是不是很尴尬? 好吧,你把文字写长点,别人说这个小小说写得还行——你是不是又尴尬了? 如果闪小说缺少小说的内核,缺少小说的质地,闪小说写作者缺少博大深厚的人文精神,缺少对社会的理解与反思,看似热闹的闪小说就会一闪而过,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大家都要裸奔。 写作技巧决定作品的下限,作者的品质与素养决定作品的上限。 飘尘的闪小说,在我看来,很有份量,是难得的好作品。 《帽子下的眼睛》。从技巧上说,这篇运用了错位的手法。阿兵要杀莫七,却被另一个人当乔五给杀了。这看起来很乱,但认真想想,又很有规律和秩序。把规律和秩序的事情用错位的方式来讲,这叫创意。平平淡淡的风景,换个角度就有冲击力。 当然,隐藏在小说背后的深意,一句话说不清楚,要用很多话来说,但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就有点违和了,所以不用说,大家都能意会。 所以闪小说也可以弄出大主题来,弄出深意来。弄出来了,就是高手,不比长篇中篇份量轻。小说讲的不是字数多,讲的是故事背后的东西,就像武林高手从来不比谁的招式多,比的是谁能一招毙命。 小说题目《帽子下的眼睛》也能给人想象的空间。这很了不起。 与《帽子下的眼睛》相比,《断水》在氛围营造上显然更讲求意境。一个给我无限温柔的人,就是我要杀的人,然后直到暮年才杀了这个人,却发现杀的就是迷恋的那个人。小说要表达什么?我倒是想起了那首老歌《掐死你的温柔》。人一辈子总会上演很多荒诞剧,有些荒诞剧让人无语,有的让人恶心,有的却让人肝肠寸断。这篇显然是在讲某种让人肝肠寸断的荒诞人生。 要在自己身上找到这种形式上的对应显然很难,小说只是某种暗喻。但显然小说又能让我们共鸣,就说明我们身上也存在过或存在着某种荒诞,甚至我们正在过着着某种荒诞人生。 《与狼共舞》的情节并不复杂,只有一个意外的结尾。相比前两篇,在情节设置上显然要弱一些。但这一篇也有其可赏之处。有两点:一是通过环境描写来营造紧张的氛围,特别是人物细微的紧张感写得很到位;二是结尾留下的思考的东西让人难忘。读到最后,读者明白了这是一个人与狼争粮食的故事。狼并不是要吃麦子,而是因为人开荒种麦子蚕食了它们的生存空间,它们只能与人为敌。这是一个讲生存的故事。这个理念不新,但写得感人,特别是结尾,作为主人公的我弹着吉他又吼又叫,看似快乐和胜利,其实我泪流满面;狼不会弹吉他,只会嚎叫,但我总在想,狼是不是同样泪流满面呢?人的泪流满面,可能是出于悲悯和良知,狼的嚎叫,只可能是悲伤和绝望。结尾写人的泪流满面,是写出了真实的人性和巨大的无奈。所以这篇看似轻,实则有想象的大空间。 《外乡人》写的是一种乡愁吗?肯定不是;写对城市的眷恋吗?好像也不是。我觉得是在写一种很复杂的无所归依的流浪心态。读第一遍,我就想起了梁鸿的《出梁庄记》,〈出梁庄记〉写梁庄出去的打工者,包括上过大学的那些普通人在城市的命运。那些人有的打了一辈子工,受了一辈子委屈;有的挣了钱,出人头地,当了老板,当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他们始终不是这座城市的一员,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籍,所以他们始终无法在心里认同让自己成功或者失败的城市;他们都在老家花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修了房,但几乎没有人真正回去住过。那所房子似乎只是证明梁庄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的根,而他们实际上又并没有人真正愿意归根。这种飘浮着的状态可能是现代城市打工者通常的心理。城市需要你付出,但又用户籍把你实质性地拦在城外。现代白领,你说他们是城市的主人?显然不是;但他们又实实在在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让为这座城市付出了一切的外乡人到死都融入不到城市里来,这恐怕也算是一种特色。 《芙蓉山主人的等待》和〈星星下奔跑的孩子〉都写得很诗意,虽然两篇小说的题材完全不挨边。〈芙蓉山主人的等待〉写一个不懂诗的人酿下美酒等一个说好还要来却再也没有来过的诗人,在祖辈的等待中,曾孙等成了诗人;〈星星下奔跑的孩子〉写一个五年没有见过父亲的孩子对于父亲的表面的陌生和心底的亲情。提到这两篇,我是想表达一个意思:作者的写作真是游仞有余,写这种诗意的东西,居然也可以写得不动声色。另外,一个老农民的曾孙等诗人结果把自己等成了诗人,还暗含了几分幽默的调侃味——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竖着排的口号就是诗吗?端着架子的就是诗人吗?恐怕最朴实最接地气的事物才是诗,最朴实,最接地气,心存美好的人才是诗人。 《尖叫》。尖叫是因为疼痛,是因为某种记忆。母亲未婚早孕,被打胎,作为未出生的孩子,她受到了伤害,虽然她最终幸存下来了,但落下了尖叫的病根。十七之后,她也未婚早孕了,于是,她又听到了尖叫,是自己嘴里发出来的。 我这样说情节,显然是出于无奈,因为老老实实不把情节说清楚,后边就没法说下去了。但这样说情节,显然是对小说的伤害,小说的迷人之处就是让你明明知道他是这个意思,但就是不能说,一说就俗了,就没意思了。 写主人公和主人公的母亲类同的故事,这是对照写法,两个故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种对照或对映的写法,强化了故事传达的悲凉感。这个故事,要表达的东西很多,但的确又是一件不好说到明处的事情。有人如果一定要追根到底,说作者表达了社会对于未婚母亲的不宽容,对于生命的轻视甚至践踏,当然也没有错,但作者肯定不是要表达那个主题,或者说没有强调批判现实主义的意思,我想,作者要表达的,应该是站在人类的高度,对于生命的理解与珍重。 另外,这篇小说还看似不经意地设置了一个情节:当主人公陷入爱情的时候就减少甚至不尖叫了。这是什么意思?我想,作者要表达的是,爱才能使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才能使我们不受到伤害,不陷入恐惧。 关于小说的“真实”。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真实是讲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在生活中找对应。孙悟空是从石头里崩出来的,绝对不“真实”,但这不成为否定《西游记》的理由;土行孙可以驾土遁,这不“真实”,但《封神演义》不失为古代优秀小说。所以飘尘小说里150岁的女侠有什么不真实的?抓这个辫子,是无理取闹。 飘尘的小说的特色,我觉得至少有几点可以提炼:一是情节设置的九曲回环。不是只转一个弯,不是只设一个包袱,在很短的文字里,常常有几个包袱,这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故事能力。二是诗意感。诗意感不是指文字的优美,是指氛围的营造给人带来的感受。哪怕是一些看似阴森的场面,读者读到的却是诗意的东西。三是抽象的能力。抽象在摄影里有两个意思:一是作品本身很抽象,有多种理解;二是摄影人能够从看似杂乱的场景里看出规律,看出规则,从而拍出有规则的作品出来。我要说的是,小说作家写小说的时候,要善于把故事抽象出来,比如飘尘写女侠的头发和身形瞬间的变化,写老头看星星凝固的姿势。这是电影的手法,把电影的手法运用到小说中来,这是抽象能力。甚至我们可以说《帽子下的眼睛》这个故事,本身也是生活中抽象出来的。 写故事写得老实的人车载斗量,但写得太实就没味道了,就像一个美女一丝不挂其实并不好看。所以大多数写作者穷其一生“著作等身”依然平庸,因为他们太局限于所谓的现实生活,没有创新的勇气甚至没有创新的想法。能够抽象生活的人,是真正的高手,是上了境界的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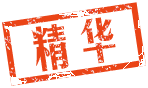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