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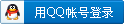
x
我怎样写小小说(作者:申平)
一、点石成金--怎样把故事变成小小说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听故事,讲故事。无论多长的故事,只要我听上一遍或看上一遍,我就能讲得绘声绘色。在一群孩子中。我是故事大王,连大人都让我唬得一愣一愣的。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装着满脑子的故事开始写作了。杨晓敏、冯辉先生评论我的小小说具有"平民色彩和故事因素".根源大概就在于此。
我开始写作,并不是写小小说,而是写长篇小说,放学以后趴在油灯底下就写,写了20多万字,结果肯定是失败了。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小小说是训练作家的最好学校"(阿.托尔斯泰语),幸亏我的语文教师张延珍告诉我,还是先写些短的吧。我便写了一些两三千字的东西,她便拿来在班上念,同学们便开始称我为"作家",这对少年的我鼓舞很大。后来,还真有一篇名叫《小虎子》的儿童短小说在辽宁的一个儿童杂志上发表了,也许从那时开始,我便和小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学时代的我写了许多儿童小说,但发表的不多,编辑给我写信,说我的作品过分追求故事,忽视人物和主题。以后,怎样走出故事的"阴影",就成了我创作中要不断克服的难题。的的确确,要把一个故事改造成一篇小说,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你在生活中发现或听到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有时它只是一个笑话。就像我们在田野里收获的庄稼,是不能直接就吃的,你必须把它加工成米面再做成食品才能吃。这个加工过程,就是把故事变成小说的过程。也就是说,故事往往只是一些原始材料,它杂乱无章,缺少底蕴,没有主题,但是高明的"厨师"却能把它加工成各种鲜美食品,供人们享用;低劣的"厨师"或者不懂加工,照煮不误,或少盐无油,根本没有味道。
我算不上高明的厨师,我通常采用的加工办法有两种,第一是给庙造神法。第二是添油加醋法。
给庙造神法。生活中的故事往往就像一座庙,你走进去,却发现里头没有神仙,也就是没有主题,这时候,你就要动手给庙造神,这样,庙也才能成为真庙,故事才能变成小小说。我的许多小小说如《红鬃马》、《怪兽》、《通灵》、《活鲁班》、《头羊》、《老张的罗曼史》等,都是按这个办法"加工"出来的。《红鬃马》是我儿时就听到的一个故事,说马群中的一匹儿马子(公马)总去和狼打架,它的武器是四蹄和马鬃,打架时,它的鬃毛会竖起来,像巨鞭一样威武有力,两只狼都不能把它奈何。但是有一天,主人无意间剪了它的马鬃,结果它被狼吃掉了。这个故事本身是好听的,但你照写下来,却没有发表价值。因为这可能只是个偶然事件,没有什么内涵。于是我对它进行了加工,把主人无意间剪马鬃改成他有意剪马鬃。他发现儿马子在跟狼打架,不但不上前去帮,而是偷偷地逃跑。然后它又把儿马子栓起来,不让它出场。儿马子高声嘶鸣,他就去用马鞭子抽它,骂它"逞能,找死"!结果儿马子用鬃抽了他个跟头,主人恼了,拿来剪刀把它的鬃毛全剪掉了。夜里,他听见外面狼嗥马嘶,但他不敢出来,结果天亮一看,槽头上只剩下半截缰绳......这样一改。主题和社会意义就出来了,人们读这篇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想到,对我们身边的人才、特别是有冲劲的青年人,不能去过分地限制他们.有时所谓的爱,实际就是害。
《怪兽》也是这样,原故事是说猎人在山上碰见了一头怪兽,怎么也打不死,最后一枪打在它眼睛上才打死了。我加工时,就加了许多所谓"山规"进去,首先神兽山就不能来打猎,接着是什么"孤猪怪兽不能打","打兽不能打眼"的许多祖传规矩,猎人一样样破了这些规矩,结果取得了胜利。小说告诉人们,办事决不能循规蹈矩。
《头羊》可以说是我的小小说代表作之一,它的原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就说一头种公羊总爱撞人,羊倌饮羊的时候它撞过来,羊倌一闪,结果它撞在石槽上,撞死了。这个故事能说明什么呢?什么也说明不了。我就把羊倌写成一个守旧势力或叫落后生产力的代表,他总看外地引进的细毛种公羊不顺眼。千方百计跟它作对,结果引起头羊的反抗。羊倌饮羊时打羊。头羊看着火起,一头把他撞翻,羊倌第二天就设了一个局,故意又打羊,看见头羊撞来他故意一闪,这就形成了一场旧势力和新事物或说落后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之间的斗争,虽然头羊死了。但它死得壮烈,发人深省。
还有一点,生活中有的故事也有一个"神",但那个神--即思想却是消极的,需要你去给它更换,这也可以叫做给庙换神法。比如《通灵》,它的原故事是讲迷信的,其中也讽刺了人的贪婪,但立意太低,我就把它的"神"换了,换成了音乐家去寻找灵感,无意间发现了黄鼠狼爬高桌的一幕,使他的创作灵感骤然爆发,这样,主题一下子就升华了。这也可以叫做"旧瓶装新酒"吧。
添油加醋法。生活中的故事有许多并不完整,需要你有枝加叶。有梗添花,但你要添得巧,加得妙,这样才不会弄巧成拙。我的另一些小小说《猎神》、《草龙》、《摔跤》等便是这么写出来的。
《猎神》是一个朋友讲的故事。说的是省射击队的几个人去山里打猎,他们的枪法使有神枪手之称的本地猎人目瞪口果。如果就这么写下来,故事会很平淡,也没有多大意义。我就又加了一些故事因素进去。说省射击队的人在镇服了老猎人以后,归途之中突遇一只熊,射击队的人一个个屁滚尿流.惟有老猎人岿然不动,他勇敢地和熊对峙,并叫大家别慌。都站到他的身后去,结果狗熊败阵而走。这时射击队的人才恍然大悟,真正的猎神并不仅仅是枪法好。这样一添油加醋。故事生动了,主题也深刻了。
《草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作品,原故事说的是马倌不认识神马—即草龙,轻易就把它卖给了别人。这本身也没有多大意义。我接着写老马倌为此后悔一生,在他临死的时候他仍放不下这件事,他仍盼着孕育产生草龙的天气再度降临,盼望草龙再到马群中间来。最后在暴风骤雨中,老马倌手抓野草死去。老马倌以一生的时间来纠正自己的一个错误,可谓震撼人心。这样故事就有了内涵.它也就成了小小说。
《摔跤》本是个真实故事,说的是县委书记和他手下一班人在沙滩上摔跤玩,过了一回平凡人的生活。故事本身有一定意义,但并不深刻。我就加了一些情节进去。说书记和手下人摔跤没有一个对手,有的人不摔自倒,他觉得不过瘾.就去和路过的一个小伙子摔,小伙子把他扛起来,书记手下的人大声喊叫,小伙子到底没敢摔他,而这个结局与当年他和县委书记摔跤的结局大不一样。他拉起小伙子就走,说我们去别处摔。他盼望和呼唤的,就是重新恢复和人民群众亲如一家的血肉联系。
给庙造神也好,添油加醋也罢,目的就是要点石成金,把好的或不好的故事改造成为小小说。这也是一门"功夫",练的好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小小说作家。
二、画龙点睛--怎样把人物写成小小说
我写小小说,灵感不仅来源于看到或听来的故事,还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些人物。我上边说的那些作品,可以概括为"故事加主题"式的小小说,而以人物为主的小小说,可以概括为"人物加主题"式的小小说。
人物加主题式的小小说更不好写,原因是想真正写活一个人太难了,并且还要通过这个人物折射出时代的影子和思想的闪光,这就更是难上加难。
我写这类小小说,采用的是画龙点睛法。所谓画龙点睛,就是抓住人物最主要的特征,就像画速写一样,以最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和性格。这正如老舍先生所说:"小小说是小说,不是随感和报道。它短小,可是还有人物,这可不简单了。写这种小说,作者要极其深刻地了解问题与人物,并能够极其概括地叙述事实,用三言两语便刻画出人物。"
我的一些小小说如《功臣》、《月白丈人》、《"闲员"许克武》、《业余"特工"》、《老吴醉酒》、《秃耳于》、《徐老赌》、《赛福兰》、《张落子》、《老冷这个人》等,都是这么写出来的。
《功臣》是我写的第一篇小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老功臣和一个小功臣的故事。小功臣喝醉了酒,将功勋章扔出窗外,骂这是废铁一块(因为政府没有给他安排工作),这时老功臣出现了.他就是平时在村里话语最少、整天和哑吧牲口打交道的羊倌"老闷罐"。老闷罐出来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功勋章从雪地里捡回来,他对小功臣说了三个字:"戴上,你!"但是小功臣又把它打掉了,老功臣再捡,他再将其击落。这时只听"啪啪"两声。是老闷罐给了小功臣两记耳光,然后一直把他拖到自己的家中,他拿出一个小盒,又说了三个字:"打开,你!"小功臣一看傻了。小盒里全是年代久远的功勋章。小功臣"啪"地一个立正,他酒醒了。这篇东西抓住一个"闷"字作文章,主人公老闷罐一共才说了9个字,其余都是动作,但这个人物却活起来了,这个人物给人的启示也是沉甸甸的,我们既为他默默无闻的精神喝彩,也为我们未能照顾好这样的老功臣而扼腕。
《月白丈人》写一个老人一辈子耳根软,总听别人的话,因而错失了许多人生机遇,但最后他终于耳根硬了一回,别人告诉他装在酒瓶里的是毒药,可他偏就去吞了几口,结果他丢了性命。这个人物的核心点就是听话与不听话。《业余"特工"》写一个人总喜欢监视别人,他的这个毛病是文化大革命时留下来的,可见"文革"余毒之深。《徐老赌》写一个以赌博为生的人,却不希望女儿嫁给赌鬼,为了女儿,他毅然戒赌,剁了自己的手指。《老冷这个人》则突出写主人公的"冷",他平时对人冷冷地不近人情,后来又冷下一颗心帮别人打官司,告贪官,终于取胜。人家要他去作报告,他上去只说了几句话,就冷冷地走了,把所有的人冷在那里。就是这么一个"冷"字,人物就活了。
生活中的人物也往往不是很完整的。需要你去添加一些东西。我的体会,生活中的人物往往是一条条的"龙",但他们往往无"睛"。它的"睛"经常需要作者给它加上去。这就是"功夫"所在。比如老冷这个人,生活中确有其人,两次"闹宴"的事情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一直想写他,但一时看不清他的"眼睛"在哪里。后来我给他加上了打官司和讲用两个情节。终于给他点了睛,这个人物就活了。这篇小小说不仅被选人《小小说选刊》,还被选人《2003年最佳小小说》中。
"人物加主题"的小说如果写好了,可能生命力更长久,因为文学毕竟是人学,读者最容易记住的不是故事,而是人物,是"这一个"人物。
三、电火石光--怎样把意念变成小小说
把意念变成小小说,好像有"主题先行"的味道。但在创作中,我体会到这也是一种写作手法,有时也很管用。
所谓意念,是指你在生活中偶尔发现的一些心得,一些思想闪光,一些带有哲理的片断等等。这些灵感往往犹如电火石光,稍纵即逝。如果你不留意,是根本抓取不到的。而你一旦抓取了,你就要找个或编个合适的故事做载体,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手里有了神,要造个庙把它放进去一样。我的一些作品《杀牛》、《打牌》、《井绳》、《选丑》、《水哨》、《清淤》、《惶惑》、《窗外,那棵杏树》、《活人让尿憋死》等,都是这么写出来的。
文革期间,我亲眼看到由于"左"的路线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对所谓"黑五类"人员特别不公,这些人无论做了什么事.只要被人稍加歪曲,就可以招致一场批判。如果讲人权,这些人是最没有人权的。这个"意念"在我的心中隐藏了许久,这天有人说到农村杀牛,好人是不杀牛的,因为杀牛被认为是缺德的事。我眼前灵光一闪,立刻感到那个"神"有了安身的"庙",我立即动手写了《杀牛》,说过八月十五,大家都想吃牛肉,却谁也不肯去杀牛,这时就有人提让富农分子魏老八去杀。魏老八不干,众人便逼他,说他不让贫下中农过节,魏老八无奈,只得含泪去杀,杀完他嚎叫着跑了。大家这天晚上吃完牛肉,又开始说魏老八心黑手毒,要开会批判他。通过这样一个惨烈的故事,充分写出了人性恶的一面,较好地表达了我的那个"意念"。
《选丑》的意念来自在单位不敢说真话。我编了个故事把它装进去。是说在科里科长本来最丑,大家开玩笑,说咱们今天选丑,谁丑谁请客,但选举结果却生最帅的一个小伙子。《惶惑》的意念来自一些成人考试,过去抄袭是最可耻的,现在不抄袭却成了傻瓜。我设计男女两个人物,说他们小时候在前后位,男生因抄袭而成罪人,现在长大了,他们又坐前后位考试,男生却因拒绝抄袭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反差如此强烈,他惶惑了,我们也惶惑。《窗外,那棵杏树》,灵感来自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用的着的东西趋之若鹜,用不着的东西无人理睬。《活人让尿憋死》是因一次听报告我坐前排,因不好意思离席而尿急,当时就想,看来活人让尿憋死也是有可能的。我就设计了一个一心想往上爬、想让领导看到自己的人,坐在那里听一个又一个领导讲话,偏偏这些领导一个比一个能说,结果真把他给憋死了。不仅讽刺了这样的小人物,也对会风提出了批评。创作中的这些意念当然不是孤零零地来到的.它往往也伴随着人物或故事出现,只不过是在人物或故事成形之前.它就已经很清晰了,使你如梗在喉,不吐不快。这和那种先确立主题然后再去找生活的"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并不是一回事。
四、"言之不明"--小小说创作的最高境界
以上我说的三种小小说的写作方法,很可能不登大雅之堂。而且,这三种创作手法,有时一下子也很难分得很清楚,它们有时是独立到来,有时却又是结伴而来。
这里我要说的是,有的故事或人物进入你的创作视野。你也感觉到了它的内涵所在,但那个"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你却无法说得明白,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言之不明"的境界,有人称它为小小说的最高境界。正如美国当代作家约翰.莱尔乌克斯所说:"从本体论上说,小小说是一种艺术鉴别力的操练,它可以拉紧环绕着我们所知事物或我们认为自己所知事物的神秘圈......,一篇真正的小小说,不管其他方面如何,应当是一个令人百读不厌的故事。不过无论我们阅读多少次,都依然不能彻底理解它。"这就是说,一篇好的小小说决不能像一碗清水,让人一眼看到底。这碗水应该是五光十色的,首先它很吸引人的眼球,然后它又是深不可测的,让人无法看清它的底在哪里,而且这碗水还应该是五味俱全的,张三喝一口说甜,李四喝一口说苦,王五喝一口说辣,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体验,这样的小小说才可称为上品。
我的小小说中缺少这样的上品,但也曾有意无意作过这方面的尝试。《大仙姑》应该多少有这么点意思。县城的老君堂里有个大仙姑神像,"文革"时人们用牛拉都拉不倒,若干年后,神像被雨水冲坏,秘密才显露出来:原来神像塑在一根树桩上,来看的领导不让泄露这个秘密,却在树桩上重塑神像,一时香火大盛,该县成为旅游贸易中心。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到现在我自己也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来。
还有《古坛》和《绝路》两篇。《古坛》写家里有个清末的坛子,本来只能腌鸡蛋,但朋友来要,就以为是宝贝,到处去鉴定,说不值钱还是不信。后来,坛子被打了一条纹,才想起送人,但却没人要了。《绝路》写一对男女路上调情,没想到前面洪水冲断了公路,他们险些连人带车栽进去,他们往回返,一路上见车就拦,说前面路断了,却没有一个人肯听他们的。这种小说的主题,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惟其如此,才如嚼槟榔一样有味道。
我感觉,写这类小小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不能刻意追求,更不能故弄玄虚,故意让人家看不懂。否则,便会走到邪路上去。
五、语言和结构—小小说精短的秘诀
我们读小小说,第一接触的是它的语言,第二注意的是它的故事结构。语言是它的血肉,结构则是它的骨架。作者只有把这两点把握好了,才能真正把小小说写短写好。
有人说,小小说应具备三个特点:即小说的情节,散文的篇幅,诗歌的语言。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说它要用诗歌的语言来写,并不是说它要合辙押韵,而是指它的凝练概括性,鲜明生动性和跳跃性。
首先它叙事要简捷明快,直截了当,一般不进行具体描写.即使有描写,场景和画面往往都是浓缩的,点到为止的。我写小小说,总是千方百计地"长话短说"。我的一些作品.如果拉开来写,完全可以写成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比如《红鬃马》、《猎神》等,都可以写的长些,但我都用了一千多字便结束了战斗。我摒弃一切没必要的描写,用最明白简练的语言告诉读者我的故事,实在要描写了,比如红鬃马的鬃,我也只写了一句话:"夕阳也照着它的红鬃,那顺着脖子拖下来的长长的鬃毛一跳一跳,正如一团火焰在燃烧。"我觉得,这就够了。
第二。语言一定要鲜明生动,要有自己的风格。我不敢说我的语言有多鲜明生动,但起码我的语言比较平实,比较幽默。人家读我的小小说,往往会捧腹大笑。这种幽默不仅指的是某一句俏皮话。而是你所营造的那种语言氛围。比如我写《杀牛》,开头这样写道:"牛肉。炒牛肉,炖牛肉、牛肉馅饺子,牛肉丸子。月亮爬上半天央,大家还端着盆子在那耗着。或蹲、或坐、或站,把蛤蟆叶子烟嘬咕了一地;一边假装吞烟圈往肚子里咽唾沫.一边在心里合计分到牛肉咋个吃法。可牛呢,还他妈的没有杀倒。"本来是很闹心的事情,可经这么一叙述。就让人想笑起来,这也许就叫黑色幽默吧。
第三,语言要有跳跃性。诗的语言讲究跳跃,小小说当然也可以跳它几下。比如我写《惶惑》,开头是这么两句话:"那件事他永远忘不了。这件事他永远理解不了。"等把两件事说清楚了,最后又把这两句话重复了一遍。诗歌往往也有句式重复,这样。给人的印象就更为深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意境,是留白艺术。写诗最讲"功夫在诗外"。讲"言有尽而意无穷。"写小小说,也应该讲究这些。说白了,就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要给读者创造一个想象空间。仍以我的《红鬃马》为例,最后的结局是马被狼吃掉了。这里也可以写马的尸体或剩下的骨架,写血淋淋的场面。但我没有这么写,我写道:"主人骑马去找,他走过山头,希望再看到儿马子对着红日嘶鸣;他走过山岗,希望再看到儿马子与野狼搏斗,然而他只在草地上发现了血迹(现在看,这句话也是多余的)。主人对着草原呼喊,草原沉默,冷冷地把他的声音抛掷回来。主人不由浑身发抖。远处,传来得意的狼嗥"。我觉得这就创造了一种让人反思、让人揪心的意境,特别是最后一句话,给了读者充分思考想象的余地。
关于小小说的结构,我的体会是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切入点,二是点线的有机结合
短篇小说本身就是生活的横断面,而小小说选择的横断面就更小,这一刀从哪里切入,十分关键。我的直接经验是,第一刀最好挑最热闹的地方切,一刀下去,立即抓住读者的日艮球.几句话就把故事的来龙去脉弄个"大概齐"。举几个例子说:《功臣》开头这样写道:"村子里出了事,刚退伍不久的二等功臣王连生在撒酒疯!"正因他撒酒疯,才扔了功劳牌子.引来了老闷罐。这对短篇小说来说,应该是高潮的地方,要在前面做许多的铺垫。但小创、说不一样,小小说上来就介入高潮,又如《怪兽》,第一句话说:"他第一眼看见那兽,就料定自己今天必死无疑,谁叫他犯了山规。"同样,也直接进入高潮。
当然.不一定所有的小小说的开头都这么写,不可能干篇一律。有的可以设置一个悬念,比如《铜佛金心》:"几经辗转。我们终于又搬回父母住过的老屋来了。便有人来敲门。谁呢?"有的可以介绍人物,比如《月白丈人》:"人人都叫他月白丈人,其实他是光棍。'月白'的意思大概是叫的白叫,听的白听。"有的开头则点明故事的"核心",如《爷爷的毡帽》开头是:"爷爷那顶毡帽是我家的耻辱。"《老张的罗曼史》开头是:"说起来。老张的罗曼史就是与众不同。"总之开头一定要开门见山,绝不能拖泥带水。
所谓点线结合,讲的是小小说的结构。小小说的结构有多种多样,但我常用的是点线结合的办法。所谓点,是指故事的"核",或叫"中心事件"。杨晓敏、冯辉先生在评我的小小说时写道:"申平的小小说的精短取决于他的结构方法。他的大部分小小说是点式结构。即聚焦于一个简练的情节,一切都通过这一个情节去表现。(以一斑而窥全豹。)这个方法并不复杂,但困难在于,选取这个点要有质量,它要投射出较浓厚的思想蕴涵和较深广的人文背景。"例如《爷爷的毡帽》是爷爷的毡帽里是否有钱;《通灵》是黄鼠狼爬高桌等等。有了这个"点"或叫做"核",你就可以发挥想象,"放射"出一些线来。这个"线"就是情节的发展、思想的延伸。爷爷的"毡帽"所放射出来的,是人情的冷暖;黄鼠狼爬高桌,放射出来的是人生就是攀登、创作也是攀登,靠别人铺平道路是不可能的。
以上这些,是我对小小说创作的一些粗浅认识,是一些直接经验的总结,倘若稍有价值。则我幸甚至哉!
申平,笔名灵羊。内蒙古赤峰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历任林西县志编修、赤峰《红山晚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等职。1997年末南下广东惠州,任《惠州晚报》副总编辑、惠州市文联秘书长。198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0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200多万字,著有中篇小说集《追赶太阳》,短篇小说集《独狼》,小小说集《怪兽》、《头羊》、《红鬃马》等。小小说作品多次获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蒲松龄文学(微型小说)奖和年度评选一等奖,作品集连获郑州市小小说学会优秀文集奖。任编剧的少儿电影《戴佛珠的藏娃》获广东省“五个一”工程特别奖,中篇电视剧《你好,西拉沐沦》获第十八届飞天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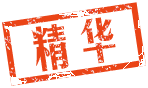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