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有醇香
唐俊高
不曾想,跑一趟数千公里之遥的新疆伊犁,竟像扣开了一坛窖藏多年的伊力老酒,收获的是一份弥漫胸怀的浓浓醇香。
我和家人驱车到新疆乌尔禾,刚游完魔鬼城,就接到一个电话,风风火火的,“唐老师,我是刘武洋,我就住在伊犁!伊犁的气候最好,景色最美,文化底蕴最深厚,没来伊犁还不算来新疆,你必须来!”
我当即被这一通电话给“唬”住了,为着此次远足的难得,为着伊犁的诱惑,更为着武洋那一番不可推辞的热切。一合计,路程虽达七百公里左右,但新疆的天黑得很晚,大半天时间足矣,便很快回复:“马上出发,再晚都赶到。”并约定,见面地点就在伊犁高速出口巴彦岱。
奔行在新疆茫茫戈壁,心胸真是辽阔着大地的辽阔。而眼界所极之处,是地平面所圆成的一条弧线。蓝蓝的天幕垂下来,与地平弧线一对接,天空就真成了一个穹顶。洁白的云彩顺着天幕垂下来,垂到地平弧线了还继续垂下去,天幕与弧线相交之处,彷佛又成了天之尽头、地之边缘,人,就彷佛奔行在了天边……
这武洋,怎么就跑到这天边来了呢?还一留就是近二十年,还把家人及户口从四川老家迁了过来。当年失魂落魄的他,或忍着风霜雨雪,或耐着酷日焦渴,这一路的坷坷坎坎,是怎样迈过来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吧,我到资阳日报社做了副刊编辑。在编发稿件的过程中,渐渐熟悉了“刘武洋”这个名字。从旁得知,他干过农活,从过军,当过杀猪匠,后被乡文化站临聘。一天,有小兄弟领着一对凄凄惶惶的小夫妻来见我,说是刘武洋夫妇,我与他才算是真正见上了一面。原来,他被精简了,试想着能否到报社来谋个职。我体谅夫妻俩低迷彷惶的处境,看重武洋脸上晦暗中犹存的那一丝筋韧,但我深谙当时报社的状况,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有好几个文笔不错的小兄弟,我都没能“安插”得下,好在那时有资阳本土哥们杀进云南报界开疆拓土、力闯天下,也好在那时云南的报业发展风起云涌、竞争白热,在大量上人,我便把那几个小兄弟一股脑儿给“批发”了过去。于是,我鼓励武洋,“为男儿,志在四方。要走,就走远点,干脆我介绍你去云南!”武洋便是这样背井离乡,悲壮成行。先过去的小兄弟些,已经站稳脚跟,已能出手相助,武洋与他们结下了生死情谊。可后来,有小兄弟透露说他在那边情况不妙,好像是得了啥病,还较严重。似乎又还很不走运,拖着病体去过三家报社,而那三家报社又似乎因他这病坨坨的到来而先后倒掉……再后来,2000年吧,我接到过武洋的一个电话,说他已经去了新疆伊犁,却不是从文,而是改弦经营小买卖。我在《中国地图》上一查,发现伊犁在那雄鸡一样的版图上,已处于雄鸡尾部那“翘翘”上,况且已是那“翘翘”的边上了。当时我心下很是沉重,想他必定是走投无路了,才从一处偏远的地方,跑到另一处更为偏远的地方去了。
可以说,我与武洋,似乎就那么一面之交,再,就是“顺手”把他“支”到了边陲云南。那次似乎同他小两口吃了一顿饭,似乎是我结的账,已记不清楚了。还可以说,时间已这么久远,他于我,我于他,可能连双方的形象都均已模糊散淡。但我这“老师”,他是一直认着,平日里除了偶尔在网上“碰碰面”,还不断有文章发回来,在家乡的报刊杂志上刊发,似乎在表明,他的初心仍未被磨灭,仍未轻易更改。
车出巴彦岱收费站,虽已是晚上十一点,可伊犁的天,还刚刚擦黑。一个灰色的人影,一边打着手机,一边东张西望,还一边跌跌撞撞地奔跑着迎了过来。我大喊一声,还果真是他。“让我好好看看让我好好看看,长成啥样去了?”那个依稀的武洋,又真实地出现在了眼前,我不由得仔细打量了又打量。黑了,夜色下显得更黑,不过,身体倒还显得壮实。“走,走,走,”他连声热切相邀,“到我那里去到我那里去!路上解决夜饭。”
结果,他家并不在这伊犁州府所在地伊宁城,而在下面的一个县,叫特克斯,还有一百余公里。好家伙,为了接我,居然专门喊了个小车,跑了这么远的路。我有点埋怨他,“现在有了导航,你发个卫星定位,我不就能直接到达你家门口了?”他却不这么认为,理直气壮地连声否认,“这是两码事这是两码事!让你找到我家去,跟我接你到我家去,有着本质区别。别人听说了,特别是老家的人听说了,绝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说。这是礼数!”不想,从伊宁到特克斯,整条道路都在改造,沿途坑洼遍布,尘土高扬,途中还要翻越天山特克斯达阪,我更于心不忍他跑此一趟,可他还是那样笃定地认为:这是礼数,这是礼数。
这次,我才算是真正认识了武洋。武洋原来是一个心扉敞荡的人,甚至是一个说话做事颇有点斩钉截铁意味的人。他说,当年他带病从云南昆明来新疆特克斯,本是给别人开车,可不到半年,他竟把生意看懂了,便同妻子一起,直接深入到乡下,在一个大队部(村委会)所在的山口,张罗起一个日用百货小商铺。当时那边牧区、农区的经济大为好转,对日用百货的需求与日俱增,两夫妇不分白天黑夜地把货品从城里搬上山再卖出去,累得吐血。那边是哈萨克人聚居区,两夫妇每天一开门就同他们打交道,“他们很纯朴,很讲礼数,我们很处得来。”有时,有哈萨克老乡提出这样那样要求,需要这样那样货品,哪怕是大雪封山,他都打马进城,况且哪怕是找遍全城,也尽心尽力地满足他们。“我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交上了朋友。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特别有情有义的日子。”后来,城里有一个带住房的商铺店面要出售,靠着朋友们的支助,他毅然买了下来,干起了批发兼零售。此后生意更好,好得来开始用大货车一车接一车地进货,自己也买了个小货车一车接一车地出货,甚至好得来有时一天劳累下来,晚上连数钱都没心思、没精力了,“搞不好,一数就是一个通宵!”他还把他目前的家产一项一项地加给我听,得出了一个庞大的数据,挺吓人的。“我是不会藏着掖着的。云南那边有兄弟伙对我的状况,是十分清楚的,我啥都要给他们讲。我还跟他们讲,如果在报社操不走了,就到特克斯来!没本钱,不要担心,来嘛!没路子,不要担心,来嘛!拖儿带女,也不要担心,来嘛!我会加倍地帮助他们的。”
对于第二故乡特克斯,武洋简直赞叹得唾沫飞溅:南有天山北有乌孙山,中间有特克斯河;境内有丘陵有森林有草原,没得酷暑没得污染,“更神奇的是,连蚊子都没得!”年平均温度才5度,蒲叶扇用不上电风扇用不上空调更是用不上……
当然,他最最称奇的,是特克斯县城。这可是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命名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八卦城”,还是被国务院命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整座城市以一座八卦坛为中心,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个卦相命名的八条大街,由内向外辐射而去。到二环路时,街道成了十六条;到三环路时,又成了三十二条;到四环路时,还成了六十四条。出自周文王乾坤学说的八卦“后天图”,竟以如此宏大规模的民生建筑,给予了另类有形呈现。我就为武洋连连感叹了:难怪不得,来到了这么一座神奇的城市,咋还舍得离开呢!
不过,我又很浅薄地在思考另一问题:源自西周易经的八卦(先天八卦),分别代表八种基本物象:乾为天,兑为泽,离为火,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艮为山,坤为地。及至周文王的乾坤学说(后天八卦),有了“后天图”时,他的认为却是先有天、地,天、地相交而生成万物,天即乾,地即坤,八卦其余六卦皆为其子女:震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一代又一代的特克斯人,为何自南宋起,就在不遗余力地按照周文王的图象,垒筑、拓展、固守这样一种形态的城池呢?我有些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不应该是在简单地按图索骥,应该是在讲求象天法地、阴阳为序,祈求祥瑞普降、逢凶化吉等等的同时,又因此地实在是地广人稀,而在特别祈求天地作合、人丁兴旺。一问武洋,似乎还真是这样:特克斯幅员面积八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却仅十七万,其中汉人三万多。有趣的是,汉人多是外来的,外来者中多是四川的,四川人中又多是他老家乐至县的。外来的四川人,大多集中居住在一个叫“阿特恰比斯”(哈萨克语,意即“跑马场”)的村落,兴盛时人口多达近九千人,村上甚至还举办过高中,考上大学的子弟至今已达一千八百余人。村子不仅成了新疆最大的“小四川”村,而且成了天山深处声名远播的“状元村”。对于特克斯如此仁厚的包容性,他也感叹,“确实,即使到了解放后,这片土地,对‘盲流’都仍还敞开着胸怀。”
武洋向我讲到了先期从他老家过来的一个人:小盲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吧,老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一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被饿出了家门。他见车就爬,爬了汽车爬火车,爬了火车又爬汽车,最终像一枚断了线的风筝,稀里糊涂地漂落在了这么个天远地远的地方。当地人一夜醒来,见突然冒出那么个浑身稀脏的汉娃子,都傻眼了。你说他是匪盗吧,不像;你说他是敌特吧,也不像。最终才搞清楚:哦,盲流。这里的地,广得种不过来,粮食有的是吃,羊皮袄有的是穿,村民们二话没说,笑嘻嘻地收留了他,帮他搭起了地窝子。可这小盲流并不简单哪,人家有文化——念过书,写得起字,还计算得来阿拉伯数字,于是,被委以生产队记分员。几年后小盲流衣锦还乡,在老家人的眼里,成了在天边有粮吃不完、还当了“干部”的新贵。于是,当小盲流返转时,就有人家撺掇一个闺女,跟他去那美好的天边成家。那闺女第一眼见到地窝子时,如遭棒击,大呼上当,差点打道回川。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大形势的好转,小两口硬是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地窝子换成土坯房,土坯房换成砖墙房,挣得了一份令老家人真正眼羡的生活。而那小盲流也实在是很争气,后来居然被一政府机关录用,成了真正的国家干部,吃上了国家粮……
可惜,当年的小盲流退休后没几年就去世了。当年那闺女,现在已是一个慈眉善眼的老太太。她总是教导后来人,尤其是像武洋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么好的地方,只要有手有脚,哪有找不到吃的?只要为人实诚,哪有讨不到好光景的?
“这里人口虽少,但民族众多,民族种类达三十三个。”武洋说,“实际上,我们汉族在这里应算是少数民族。可我们都相处融洽,因为大家都很讲礼数,这就构成了质朴的民风。”
他说,这里的民族老乡,与老家的乡亲别无二样。他们在山口开店时,那里不通电,照明靠点马灯。那只伴随他们艰难岁月的马灯,至今还悬挂在他们家里,成了“镇宅之宝”,成了教育儿子的物证。那里还不通水,一到冬天,吃水得靠下到河里去砸冰窟窿取水。有一次,他冰窟窿没砸开不说,还突然晕倒在冰天雪地里。是一哈萨克老乡,把他救回了家中。受人一尺,敬人一丈。有一次,天突降暴雨,河水猛涨,一老乡连人带车被困河中,只得在车上支起篷布躲着,苦苦等候大雨停歇。妻子小兰煮了一大钵汤面,武洋脱掉长裤,冒雨涉水把那热腾腾的汤面,送到了老乡的手上。还有一次,一老乡的巴郎(儿子)夜里突然患病,是武洋立即开车下山,送进城里医院抢救脱险的。事后,那老乡教他那小巴郎喊武洋为“爸爸”,喊小兰为“妈妈”……
我也注意到过,走在街头的武洋,黑黑的面庞,墩墩实实的身板,一副劳动者的打头,谁还看得出他是一个外来者呢?就一个普普通通的特克斯人嘛。
在天边,感受至深的,还真是那无处不在的礼数。
为了能使我在特克斯游玩尽兴,武洋特地邀请了一个叫丁昌明的当地作家作陪。丁老先生已七十有五,南京人,早年从部队转业到新疆建设兵团,就长年在特克斯屯垦,后调入地方工作。老先生居然不辞辛劳,也随武洋一道,跑到巴彦岱出站口来接我,还送上了他写的六本书,此后一步不离全程陪同。老先生的笔触,总是在新疆大地滑动,字字句句总关情。老先生说,他正着手把在伊犁的几个军屯团写成一本书,既要写艰难历程中的地窝子,更要写今天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他已实地采访了各团,尽可能地采访了各团的历任团长,只等下笔了。在5A级风景区喀拉峻大草原,管理方一听说武洋带来了老家和本地的作家,竟绿灯大开,免费放行。路边的一个院落,真正已经是红杏出墙,武洋像回到自己的家了一样,推门而入,领我们去摘红黄香艳的杏果,主人家满心欢喜,竟还给我们搬出了梯子。在阿特恰比斯村,乐至老乡见了我们几个老家人,立马丢掉他们在特殊环境中,靠自己特别的语言天赋“组合”而成的“哈川普”(一种以川话音调为主,融入哈萨克词汇、新疆方言的“普通话”),换成地道的老家话与我们热情攀谈,“你们是四川哪个凼(地方)的?”一个姓张的乐至老乡,此村的副主任,一再热情挽留我们吃饭,“天远地远的,老家来了人,我们再怎么饭要招待一顿噻!”在八卦坛,我被展柜里的一本书一下子吸引住了目光:《跑新疆》。那一个“跑”字,恰恰契合了我对小盲流、刘武洋,甚至历朝历代远徙这天边的外来者的探究心理。从作者的署名“刘敏”来看,应该是个汉人。向武洋一打听,竟还是个四川老乡,竟还就住在这城里。我当即请他代我上门去求一本书,他满口应承,“没问题,我们是文友!”显然,在他周遭,还聚合着一大群当地文朋,结果他不仅把书求来了,还把人请到了晚餐桌上。刘敏先生祖籍四川广安,自幼便随流来到这里,现为作家、剧作家,还是中国书协会员。他与我年纪相仿,但对那个“跑”字的认识和体察,自是另一番的深刻和独到。他说,《跑新疆》实为三部曲,目前还只出了第一部,就有影视公司找上门来了。武洋上的主菜,是哈萨克老乡待客最高规格的“烤羊娃子”,上的酒是新疆最好的伊力特曲。作为特克斯八卦城文化的研究、传承、推广人,刘敏先生自然是对哈萨克老乡招待客人这“烤羊娃子”的礼数,作一番仔细讲解。特别是对我这么个一头雾水的主宾,面对这一佳肴所应走到的礼数,更是一番悉心指导。就着纯美芬芳的伊力特曲,斯文儒雅的刘敏先生还主动给我们唱了一首哈萨克民歌,那歌声情意真切,韵味悠长。我也即兴回敬了一首老家俚歌,还躁动一桌子的人都来帮腔,但未免过于刚烈和燥辣,几可算是笑料……
而对于我这从老家来的“老师”,武洋的礼数更是周到、细致,点点滴滴都体现出一心一意。他变着花样领我们出去游玩,出门时要上楼来请,回来后要送上楼至门口。还变着花样让我们品尝特别美食,吃过“烤羊娃子”后,还居然安排过两只硕大的牛蹄。住宾馆、吃饭、游玩,就连洗车、给车换机油等等一切,都不要我花一分钱。有一次我都已经把钱给到老板手上了,他是不容分说让人家退给我了的。他还给我打过洗脚水,我洗了脚后,他还要争着端去倒,慌得我真正是手脚无措。临别,除了送我伊力特曲,还托我给家乡的好友带两大箱回去,把车子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甚至,他还要打发“路费”……
礼数者,有礼有数也。古话说,施恩求忘,可我认为我对武洋这样的小兄弟,并未给予啥恩惠,更没有值得去忘却的东西,他能有今天,靠的是坚韧和实诚,所以面对武洋,我是从心里感到十分忐忑。唯一能令我的心稍觉安稳的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体察到,他两夫妇并非只对我这样,他们对所有的来客都是这样仁至义尽。但,对于像武洋这样的受恩必报,在时下这个社会,多多少少确确实实又让人觉得似乎有些久违。礼数,那可是维护伦理、维护秩序的规范,不可失,不可坏,不可废,不可断绝。在武洋身上,在像武洋一样远在天边的那一群人身上,所存留的礼数像一条条经纬,维系着自己,也维系着别人;像一缕缕醇香,芬芳着别人,也芬芳着自己。
通讯地址: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资阳新闻传媒中心
唐俊高
电话18111109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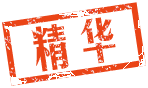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