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娘
作者:邹光耀
一天夜里,我兀自清理床柜,一双灯草绒面料的手工布鞋,不经意间跳入眼帘。我俯身拿起它,仔细端详,这是母亲年逾古稀时亲手缝制的千层底布鞋,也是母亲给我最后的布鞋。尘封多年的记忆泉水般涌来。
母亲十九岁那年嫁给了我父亲。孤儿父亲,借用叔娘的一间破瓦房拜堂成了亲,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贫困生活,陆续养育了我们六子妹。
上世纪大办钢铁的年代,父亲远走炼铁,留下母亲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为照顾年老多病外公外婆,母亲搬回娘家暂住。
那是农村“伙食团”的饥饿年代。正值荒月时节,三个面黄肌瘦孩子整天未粘一粒米,饿得直哭。
趁着夜色,母亲悄悄来到一块胡豆田,摘了半背篓胡豆叶回家,用开水焯了胡豆叶,放上生盐,三个孩子急忙围了上来,抓起胡豆叶就往嘴里塞。正在此时,三个大汉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将母亲强行绑到生产队晒场。
煤油筒子照亮了晒场,社员从四面八方赶来,母亲被绑在石柱上,耷拉着头,披头散发。妇女队长主持批斗大会,以偷盗集体粮食的罪名,呵斥母亲下跪认罪,见母亲一言不发,妇女队长就用坚硬的硬头篁暴打母亲的头和身子,用凉水将昏迷的母亲一次次浇醒,直到母亲血肉模糊。
父亲赶回的时候,母亲已卧床两天滴水未进,父亲托人写信给当兵的舅舅求救,舅舅从云南寄回特效药“一枝蒿”,母亲服用后,半个多月才闯过了鬼门关。
三年自然灾害后,陆续有了我和弟妹。1976年冬,我们家才搬进新修的三间土坯茅草屋。
母亲有一双皲裂不癒的手,每到冬季,纵横的裂口布满手心手背,疼痛难忍。凭她的这双手,侍弄一年四季的庄稼、蔬菜;饲养着家禽家畜;掌起一家人的油盐柴米;抚平苦难岁月的伤痕,将一个个孩子养大成人。
母亲目不识丁,她常年经营着十几个坛子的泡菜,掌管着一大家子充当粮食的咸菜。生产队的接待大多落在我们家,客人都说母亲的咸菜醇香爽口,顶了四分粮。一年四季,母亲起早贪黑照顾着自留地,时令蔬菜长得旺实。使我们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土地到户,勤快老实的胞兄三十出头,人不丑,心眼也实,但婚事没门。母亲说,人穷志短呀!
那年初冬,母亲占了种小麦的八分地,栽上了大头菜。一个人整日在地里劳作,担粪挑水,除草垒土,眼看丰收在望,一家人喜出望外。
天刚蒙蒙亮,单薄的母亲挑一担粪出门,哪知在跨越一条水渠时,一阵头晕,母亲摔倒在坚硬的渠道里,粪水当头泼来。母亲的手腕、手臂淤血红肿怎么也不肯去医院,疼痛得满头大汗。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第一次住进了医院。
母亲的左手腕、手臂、肩锁骨三处粉碎性骨折。
大头菜提早一月上市,卖了个好价钱,卖菜的收入父亲都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自怨自艾,心痛手术的大笔开销,急着出院。
两月后,母亲左手缠着绷带,领上胞兄去了镇上,从头到脚给胞兄置办一身体面的衣服。
胞兄终于对上了相结了婚。不久,嫂子就闹着分家,母亲把新修的三间瓦房给了胞兄,因婚事欠下了大笔债,母亲和胞兄平分。哪知后来嫂子不学好,跟别人好上了,小家闹得鸡犬不宁,最后离婚。为此,母亲还完了整笔婚债,渐渐地眼花耳背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最小的三子妹也陆续成家,各奔东西。
年迈的母亲和父亲留在了老家,仍然耕耘着儿子们撂下好几亩土地,我长期在外打工,每月寄很少的钱给父母周转零用,春节期间才回老家探望父母。短暂的相聚,总是听到母亲对儿孙辈的牵挂念唠。每次,她都准备了小榨菜油、花生、土鸡什么的,装满了编织袋。临别,无论如何叫我拿走。母亲送我好远一程,然后站在山坳上,扯开嗓子叮嘱,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常回家来。直到我消失在山嘴,忍不住心尖打颤。
2007年秋,酷暑持续未退,与母亲风雨同舟半个世纪的父亲突然离世。这猝不及防的打击,几乎叫年老多病的母亲没缓过气来。
料理完丧事,面对坐在墙角形容枯槁周身哆嗦的母亲,我无言以对。此时,我才发觉,母亲的背驼了,娘,真的老了!
我执意卖光了母亲的粮食、家禽家畜,将母亲带到小城的我家居住,母亲只好作罢。然而,不到一年,母亲托人打来电话,无论如何得回老家一人居住。
电话里,我问母亲许多话,好言挽留。母亲全盘否定,几乎带着哭腔,求我答应她回去。
母亲打着被卷回到了老家。她仍然操起了老把式——栽蔬菜、种粮食。固执地耕耘那片瘦薄的土地。
三年后,高烧持续不退的母亲患上了肺癌,在端午节那日凌晨,母亲再也没醒来。
在清理母亲遗物时,我们在一双崭新的手工棉鞋里,发现一个塑料袋,解开几层,一小叠钞票露了出来。点数,刚好是我三年来寄给母亲的所有生活费。
一旁的小弟告诉我,娘不让我告诉你,她在城里时,你家里人没给个好脸色,饱饭都没吃过一顿。
我愣了好一会,声音哽咽,娘!娘!我的错呀。顿时,泪雨滂沱。
通讯地址:荣县旭阳镇环城西路94-10-501
电话:18990092575
QQ:270009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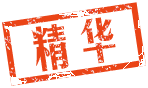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