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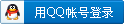
x
本帖最后由 雨巷明月 于 2016-11-2 10:35 编辑
希望唤起疗救者的注意
——读杨世英《傩戏闪小说九章》(1279字)
文/谢振
杨世英的《傩戏闪小说九章》包括《预谋》《卖牛》《招聘》《女关公》《木爷》《眼睛》《守》《雕刻师》《戏痴》这九篇闪小说。
这九篇闪小说着重刻画了傩戏艺人对傩戏的极度钟爱。题目既独立成篇又有内在联系,实在是不可得的一组闪小说。它获得了“新晃杯”全国侗族文学征文大赛小说奖,是实至名归的。
《预谋》写龙天云的儿子龙春本不想学傩戏,后来却又主动要学。龙春是有条件的。条件很苛刻,龙天云勉强答应了。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儿子的条件是要爹“把大烟戒了”。此闪表现了爹对傩戏接班人的重视。烟不是那么好戒的,对于一个烟杆不离身、烟龄不短(至少三年以上)的瘾君子来说,却能痛改之,可见龙天云对傩戏的挚爱。
接下来的《卖牛》《招聘》则直面傩戏后继乏人的苦涩。为招聘一个能舞刀求雨的关公,老姚不惜把相伴十年的好兄弟——牛卖给他人。应聘的汉子由于天公作美,不费多少工夫就完成任务,于是恪守信义的老姚把大部分卖牛款拿出来酬劳汉子,汉子不领不行。傩戏艺人为了傩戏而做出的牺牲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汉子最终因为感动而自愿拜师学摊戏学做人。
《女关公》为后继乏人的傩戏涂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它赞颂了为傩戏而贡献青春的女艺人。她以傩戏表演者妻子的身份而出现的,却技艺超群,巾帼不让须眉。《木爷》写八十五岁高龄的木爷为傩戏接班人而忙碌,他的旧徒弟阿新与新收弟子小明竟然是父子俩。《眼睛》描写傩戏的练习场景,老人的精益求精,小辈们的大转变都让人感到震动。《雕刻师》描写龙师傅对傩戏面具的忠诚守候,他专注于面具,不为名利所动。这一个个男女老少的纷纷亮相,让人对傩戏的发展隐隐还存留有希望!我们大体可以把这四篇闪小说看作是前三篇的一个转折。
《守》和《戏痴》描写了两代人的断裂,让人揪心。《守》写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因“挣钱要紧”而离开的林与独守传统的爹两代人的分道扬镳。《戏痴》继续拉开两代人的差距,两地分隔,在电话中,父只求悄悄地为傩戏用尽生命最后的时光,子却依然不明白。这两篇又可以看作是中间四篇的反转。
杨世英的《傩戏闪小说九章》为我们呈现出立体丰满的摊戏转折史。作品前后都写了傩戏的传承,前面的《预谋》《卖牛》《招聘》三篇虽写后继乏人但毕竟有人传承,后面的《守》和《戏痴》两篇则直面后继无人的窘困。傩戏难道真得就这样走向了坟墓?作者没有这样直接发问,但他那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无声呼号无疑是震撼人心的。中间的《女关公》《木爷》《眼睛》《雕刻师》四篇从傩戏的拜师仪式、招聘规矩、练习、表演、道具等依次写来,在沉郁中飞扬着豪情。
九篇闪小说共计5000余字,一个短篇的篇幅,却胜似一个中篇,看后让人百感交集。杨世英是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身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他熟悉并热爱傩戏。关于写作缘起,我曾经问过他,他坦言:“我写的傩戏是侗族傩戏,流布范围很小,只在一个侗族小村塞保存,用的是本民族的语言即侗语演唱,外族人是无法学的,所以它的传承是特別的艰难。”他之所以这么入木三分地直面傩戏的艰难困苦,无非就是为了唤起疗救者的注意——疗救傩戏要有传承人,更要我们大众给予适当的关注。
傩戏闪小说九章(5051字)
文/杨世英
预谋
龙天云,清末监生,曾在外为官。抗战后期,回归山寨。农耕之余,组织班子排演傩戏。
龙天云腰系长烟杆,他吸的不是旱烟叶,而是大烟泡。烟杆另有一用,敲脑袋。哪个弟子不用心学戏,烟杆疙瘩就会磕上他的脑袋。
龙天云的儿子龙春,寡言忧悒,并不跟他学戏,闲时和别人一起围山打猎。
由此三年。
“爹,我跟您学戏。”有一天,儿子的声音传进龙天云的耳朵里,使他大感意外。
“你不是喜欢打猎吗,咋又跑来学戏?”
“打猎是锻炼体魄,才好学戏演戏,爹您想想,若遇到天旱求雨,关公上场舞刀,火辣辣的太阳下,一舞几个时辰,体力不好吃得消?”
“咦,还真有心。”父亲答应收儿子为徒。
这天,戏场和两边高地聚满了人。先观收弟子,再看演傩戏。
给傩神“飞山太公”摆上三牲供品,焚香化帛后,接下来的仪式规程是:师父一手拿杯酒水,一手点燃三柱檀香,抖落少许香灰在酒里,师父喝一小口,传给弟子喝干。谓之“过香水”。
这时,龙春说:“等等,有件事情,爹要答应我,不然……”
“哪样事快说,答应就是!你个混小子能有啥事?!”
龙春的嘴巴,贴上父亲的耳朵。
那一刻,龙天云呆若木偶,愣在傩神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乡亲们不知龙春说了些啥,站在场上屏住呼吸,引颈呆望。
“好吧!”龙天云咬牙鼓腮了一阵,终于吐出了两个字。
人们看到平时忧郁的龙春笑了。
多年后,人们才从龙天云的口里得知,当时龙春说的是:爹,您把大烟戒了吧!
卖牛
牛场上,老姚涩涩地看牛,牛幽幽地看他,相对无言,欲泪。大胖伸手过来,和老姚在衣袖里捏价,嘀咕两句,谈不拢,大胖甩手走开。
“姚师傅,卖牛呀?”陈福拢来,上下打量牛,扳嘴看牙口,然后一拍牛峰包,赞道:“好牛!”陈福邻村的,勤恳实在的种田人。
“老伙计,你买牛?”
“嗯,你这牛,我喜欢!别个送了多少价?”
老姚说:“送是送了六千块,可那是要进屠宰场,我不卖!你买去喂养耕作,开这个数吧。”老姚捏着陈福的一掌手指头,表示五千元。
陈福倒退两步,瞅老姚,又瞧牛,疑惑:“为什么这样?”
老姚一下子抱住了牛脖子,脑袋倚在牛角上:“相伴十年的好兄弟啊!留点辛苦费给你,拜托好好照料他。”
“什么话?要你辛苦费?你的兄弟,也是我兄弟!就六千!”
你推我让,众人劝说,两人各让步,五千五成交。
牛走时,“哞啊——”一声长叫,苍凉凄悲。
老姚心里一酸,泪水再也忍不住……
老姚失神地走在街上。城里打工的儿子来电话:“爹,天这么热,不做活吧?”
“镇上卖牛。”
“卖了好!”
“……”
“爹啊,您总算想通了。我早说不要种田嘛!您看看,今年天旱很厉害,怕是种也白种了。等新房装修好,我就接你进城来。”
“那可不行!就算我答应你,你爷爷、太爷爷他们也不会答应,傩神更不会答应。我是祖传傩戏的第二十一代传人,得在山里演戏教戏。”
“爹,您都八十三岁了,再说年轻人都出去了的。”
“嗯,所以我才卖了牛,去找人写张广告贴街上,聘个关公,舞刀求雨啊!”
招聘
老姚接过中学校长启文递来的那杯清凉水,咕嘟咕嘟地灌下肚里,“啊——”地舒了一口气。
启文,有红纸没?给我写个招聘启事。
有啊。表舅是招傩戏徒弟吧?
是啊!招的是做大事的徒弟。这天干旱都快一个月了,必须关公上场,舞刀求雨!
以前不是表弟扮演关公吗?
快别说了,跑进城打工去了。还买了套房,哪能望靠他!唉,年轻人都出去了,戏班子也是干旱严重,奄奄一息。
启文找来纸笔,刷刷几下子就写好了。两人来到街上张贴。赶场的人就走拢来看。
——诚聘关公一名。男性,年龄30岁至45岁,体质强壮。聘用期20天(期间降雨日结清聘金),4000元包干。负责食宿。从事工作:舞刀求雨。
老姚和启文站在后面看,一个40来岁的精壮汉子挤向前去,把那“启事”剥了下来。
喂,求雨是好事善事,你扯它干什么?启文说。
嘿嘿,揭榜应聘啊!汉子边说边把“启事”折起来。
老姚上下打量他,点了点头:嗯嗯,你可以!
启文在办公室为老姚和汉子打印了协议,两人签字画了押,还找了两根木棒代刀,在学校操场上边教边学,舞上一阵。
就在这时,雷声大作,电闪四射,倾盆大雨降了下来。
这下好了,结账!老姚取出那叠牛钱,点了4000块,递给汉子。
啥?不行不行!这是凑巧!
协议已生效!老叔都演了一辈子忠义的关公,你总不能让我背信弃义吧?
汉子两眼含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拜您为师,学傩戏,学做人。
女关公
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伸长脖子看演出。
舞台上,张飞“咚咚”击鼓,关公与蔡阳战在一处。这关公,个子瘦小不打眼,却又身体灵活,纵上跃下,闪躲腾挪;“青龙偃月刀”舞得“呼呼”生风,劈、砍、挑、刺,招招狠辣。那蔡阳,人称“刀祖宗”。可这次面对关公,既欠招架之功,亦缺还手之力。他那面具里的眼睛,盯着关公的腿,眼神焦虑,不安。手里的刀,胆怯,无力。
一通鼓毕。蔡阳低声说,算了,演这么多!
关公咬牙说,不行!还有三十九招。
蔡阳说,你腿里的钢板……别逞能了。
没事!别废话,接招!
蔡阳边打边嘟囔,硬撑,自己痛自己挨!犟!
终于击完三通鼓,过上五十招,关公一式拖刀,把蔡阳斩于马下……
关公、蔡阳二人站在台上,摘下头套面具,向观众行礼。关公的一头秀发披散下来。
啊,女关公?!
徐春华——
观众叫喊着,掌声雷动。
很多人认得徐春华,年初,春华她,见义勇为,在街上救下一个小女孩,被车撞断了一条腿。
主持人跑过来,把话筒交给徐春华:请给观众说几句。
她说,我是红脸关公,这是我的丈夫,蔡阳。观众大笑,鼓掌。
她又说,这是二十多代祖宗传下的侗傩戏,我爱她!这戏别处没有了,我们天井寨还保留着。为了学戏、传戏,姑娘我,一辈子留在寨子里了。
木爷
“国际戏剧节”,浙江乌镇灵水居。来自湘西山里的木爷他们,正在演出傩戏《跳土地》。
听说师父来演出,八年前就偷跑出来打工的阿新,特意请假从嘉兴赶来,把草帽檐压低,躲在戏台后面张望。
“土地公老人家,您要保佑我们的阳春好啊!”
“阳春啊,今年好收成!寅时下种卯时生,早晨开花,夜晚结籽,谷粒像玉米,玉米大如薯;家家稻谷几百担,红薯几十窖,你们凡人吃了,个个肥得肚圆胯开,走不动路……”
“ 好啊!”看到师父表演土地公时而神采飞扬,时而夸张幽默,又见观众眼笑眉飞,掌声阵阵,阿新情不自禁地高叫了一声,台上的木爷一个愣怔。
演出结束,木爷摘下头套和面具。一位记者冲上前问:“老大爷,您高寿?”
“我呀,不高,才八十五岁。”木爷朝记者笑了一下,就急急挤出人群朗声喊道:“阿新,过来!”
“ 师父!”阿新迟疑一下,赶紧跑拢来,向木爷鞠了一躬,说:“师父您怎么知道是我?”
“ 呵呵,你那一声叫好,就算隔十万八千里,我一听便知!”
“师父,我……”
“别说了,听你那声叫好,我就知道你功夫没荒废。”木爷说着,就把身边一个精瘦的少年推到阿新面前:“这是我在傩戏进校园传习时新收的徒弟,跟你一样学戏有股黏劲,好苗子难找啊,他就交给你了!”阿新呆住了,那是他读初中的儿子小明。
木爷又说: “本来可以好好教他,但师父老了,怕得病,最怕脑血管出问题。”
阿新心里一震,赶紧拉过小明,并排着给木爷作了个长揖。
眼睛
冬天里,老人带着小儿子炳去看地。炳问,爹,怎么选这里,不上祖坟地?老人没听清,炳又大声地说了一遍。老人说,就在这里,能看到小的们学戏,演戏。
老人的墓碑夏天就打好了,刻上了我为他撰写的墓志铭。老人说,有这总结,这辈子值了!
老人是位戏师,白发胜雪,皱脸如菊。每天早饭后,老人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来戏场。看台上,一只老枫木做成的半圆形桶凳,把老人抱在怀里。老人温顺而安详,静静地坐,默默地看着小辈们学戏。老人的双耳在90岁时失聪了,听不见小辈们嘻嘻哈哈,也听不清锣鼓的咚咚锵锵。
看到小辈们学戏不太认真,舞步也不规范,还嘻里哈拉的。老人的脸,布上乌云,昏花的眼,迸出火花。老人提起黑光油亮的拐杖,在楼板上“槖、槖、槖”地点几下。
……
腊月初八,老人像一枚熟透的果,落在那个小山包上。
墓碑外面还套立有一方无字石块,只能从两边的拱形开口,看到里面碑上的五个大字:老大人之墓。
有人问炳:怎么外面还套上一块石?
炳说:坟墓的眼睛。
又问:刻碑花了几百块钱,拿给哪个看?
炳说:我爹自己看。
外地打工回来的侄子见了就气恼,嗔怨道:哪个叫你这么做?!
炳白了侄子一眼,下巴朝前一扬:你爷爷叫的,不信你问他。
……
老人去后,小辈们学戏上心了很多。他们互相说,认真点,莫胡闹,老爷子盯着呢。
一天, 我站在戏台上看到,前方山包上, 老人的墓,一双深邃的眼,静静地看向这里。
守
元宵一过,村里男女“呼啦啦”的出去了,热闹的年,喧哗的村,静默沉寂下来。
林也要走,叫爹同去。爹说,不,我放不下傩戏“咚咚推”。你也不能走,在家学戏!三十晚夜你答应了的。
哈,那晚喝高了。爹,学戏过两年再说,先挣钱要紧。您不看看寨上元灿、昌木他们,都建成了楼房,买上了小车?
林又说,爹,您都七十多了,留在家里,我们不放心,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咋办?
爹不高兴,瞪林一眼,说,我这身子骨,棒着呢!
林和妻出门那天,带走了儿子小启。爹站在尚有积雪的门口,眼神恍惚而迷离。寒风如刀,把爹脸上的菊刻得更深了。爹的身后,雕梁画栋的百年木屋,在朝阳下闪着亮光。
林走上院坪,回望老爹,心里“咯噔”一下。爹目光如线,牵扯着自己,林被定住,举步难移。
爹却笑了,说,出去好生做事,小启好好读书,不用挂念我!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会闷的。我是戏师嘛,可到别的村找徒弟。
爹笑声爽朗,林的心里稍觉安慰。
爹跑了几个村寨,村里头头都说,老伯,戏是好戏,也该传习,可年轻人都已出去了啊。
这天,春光明媚。爹身穿关公袍,手握青龙刀,独自起舞,高唱:三弟三弟把门开,我是二哥关云长……
脚步踉跄,声音苍凉。
爹沿着屋外那条青石板路,一路向前,且舞且歌,如痴如醉。迷醉中似有掌声“哗哗”响起,爹停下歌舞,颤声叫道:林他娘啊,谢谢你的鼓励!
山包上,一座芳草萋萋的坟墓,里面住着林的母亲。墓的周围,丛丛绿树,在风中摇摆,叶片翻飞、拍打,“哗哗哗”地……
雕刻师
“龙师傅,在雕傩面具?”我跨进龙师傅家堂屋时,他正坐在一张小方桌前,低头雕刻一块面具。
“哎呀,喜鹊叫,贵客到,请坐请坐!”
我就坐下,拿起那块即将完成的傩面具看,面具散发出一股扑鼻的香气。我说:“楠木做的?”
“嗯,只能用楠木。其他木材不能做,放久了,会开裂,也会被虫蛀。”
“哦,那是!这面具是啥人物?”我说。
“你猜猜?”他咧嘴一笑。
这块面具的形象,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夸张变形、怪异奇特;狰狞凶猛、咄咄逼人。我说:“鬼?嗯,是鬼!”
“太笼统了点。”
“嘿嘿。”我说:“龙师傅,听人说,天井寨傩戏表演的面具都是您做的?”
“做得不好,呵呵。”
我说:“这种面具是不是经常做?”
他说:“不常做,政府需要给天井寨添置面具了,来找我做,我才做。”
我说:“你咋不做出一批拿到天井寨去卖给游客呢?您给政府做,那是计划经济,你给游客做,才是市场经济啊。”
“会有人买?”
“怎么没人买,北京的人还打电话问着要呢。”
“哦。”
我看着头发花白的他,有些惋惜地说:“别人要有您的这个艺,早就发了,可是您,还在这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呵呵。”
“这样吧。我们给您好好地宣传一下,让您的工艺品走向全国。”
“不不,宣传不得!有害无益啊。”
我大吃一惊:“什么?有害?”
“我们这里,楠木并不多。我一年只砍一棵树,雕刻面具二十块。你倒提醒了我,我得给天井寨签个协议,我做的面具,专供演出,不能流走!”
戏痴
乡下的老爹打电话给他。
爹说,昨晚做了个梦,傩神飞山太公说我还有七天阳寿。
他一愣,赶紧插话说,不就是个梦吗?爹千万别在意。
爹说,别个说的我不信,傩神说的,我信!傩神庇佑我们的傩戏延续几百年了。
爹您近些日子演傩戏太多了吧,一心念着傩神。
爹说,傩神,“飞山太公”杨再思,拜将封侯,一世英武,公正廉明,西南各处,世代尊崇。乡民建庙,供奉香火。莫说我还演了几十年傩戏。
爹又说,傩神还说最后这几天,不让我生病,因为生病得住医院。
爹,您身体不舒服?有病可耽搁不得!还真得上医院去。
我好好的。傩神托梦让我再教几天徒弟,以后就靠他们演戏了。傩神还说,他要悄悄带我去沅江,以后我就在河底演傩戏。
爹您咋了?越说越邪乎。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想,人嘛。得讲究个魂归故土,我求傩神说,就不去沅江了,我可以自己挖座坟墓。
他急得大声喊了起来,爹,您说这些话太荒唐了!
爹不紧不慢地说,不这样也行,但你得让我死后安静地上山!我不喜欢热闹,傩神交代过我要悄悄走。你答不答应?
我答应。话一出口,他就“啪”地打了自己的嘴巴一巴掌。
那头,爹呵呵地笑,答应就好,我这一开心啊,也许能再活七十天。若你能让我省点心,也许还活七百天、七千天。
他也笑了,说,爹,难怪人家叫您“戏痴”,啧,您的这一出!爹,我保证让您再活七百天……不,七千天! |
|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