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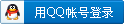
x
本帖最后由 石头 于 2012-11-25 19:58 编辑
文/石头
父亲在工地护架上走了眼,一个趔趄从三层高摔下,昏了过去。工头拉来下手扛到附近医院,正入院门,父亲啊一声惨叫弓起上身,把肘一勾门前柱子,双手抱死。扛担架的赶得急,哐啷倒了。工头甩来一声蠢货两步抢上前,喝我父亲搞啥鬼。
“妈的,我玩命钱,叫你来这儿开涮!回去!”父亲虎着黑脸,狠狠吃了工头一眼。众人抹抹冷汗瞧父亲攀着柱子立起,右腿啪啪啪蹦回宿舍。父亲咬咬牙,找出桶里早备的生石灰,倒上水,扯一段被单,浸石灰里裹了几层,往喊痛的左膝垫截棉布,将被单往膝盖铺卷几回环。大功告成,倒头呼呼大睡。
父亲的腿就是那天瘸的,那年父亲虚五十一岁,刚过知命之年。“命不好,命不好,老天害我。”蝉声伏在夏天脊背上,太阳烹着院子。父亲光着上身的肉,把着斧子砍柴。拄杖搭着泥墙。“你就不能给我争口气,再考不上,我他妈,”父亲对准一截木头,“削了你!”
父亲要强霸道,在村里是有名的。“外头,敢欠老子工钱,刀子就递上去!”父亲老叼着这句狠话。而平常家里,也就数他呼来喝去,母亲大姐二姐都狗似的让他使唤。母亲菜炒得最好,有口皆碑,独独父亲这个咸那个辣的,母亲只管宠着他那张臭嘴,从不计较。大姐二姐脑子笨,功课门门鸭蛋,给父亲气得操起能够得着的就打。
要是有人早些提醒我,你老爹这么这么个德行,我是坚决不肯落我娘肚子里的。
那年春早,乡里计生办在政府大门前摆了个摊子,催来各村各户,一个胖子歪着领带台上吆喝。台下人头攒动,像扎着一根根火柴棍。“相亲们,计划生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家要配合国家的这个好政策,不马虎,不欺骗,不侥幸!”说到“侥幸”时,胖子一脸毒笑。
“阴孙子!”父亲边骂边往家走。“就允许你抱儿子,叫我们替你省心!”父亲往山腰一望,呀,李花赶庙会似的占满了山头。父亲胸前一热,两腿紧了紧,拔开步子奔田埂,拽了母亲的泥手甩头就走。
这片梯田背靠石龟岩,传说太上老君曾驾神龟落足此山修炼仙药,得成返天庭,却留下了神龟。乡民最喜欢给山给水贴个道行,好自己长脸,其实不过一块巨大的破落石。但其下山川分裂,涌出一壶瀑布,水流哗然终年,直奔闽江去。父亲抢了母亲藏到石龟岩底荫处,干起好事。按母亲的得意说法:
“然后你就从瀑布里钻出来了,流到溪水里,滚啊滚啊,哭天抢地。你爹提着裤子一路跌下去,最后还亏你外婆有见识,编了筐竹篮,打溪里将你捞上来。”
“别听你娘瞎扯!”父亲听着局促,高瞅低看的,嘴角挂着尴尬的笑,突然指着桌上的白菜啧啧点头,“今天这菜炒得不错嘛!”
满月席花光了家酿的三缸米酒和一口雄壮的公猪,母亲心疼不已。父亲只顾敬酒,快活地拍我屁股,嚷着,“谁说我生不了儿子的,敢笑我!这是什么?”乡亲也厚着脸皮拍我马屁。父亲当我是神仙赐的,逮到啥节,都爬去石龟岩恭恭敬敬上一柱香。后来母亲跟我讲:“你哪知道那时生不出儿子,我和你爹都不敢出门,就怕被人指着脊梁骨。”
父亲歇歇斧子,擤了串鼻涕,扭头朝我喷口水,“可你净给我屎吃。你叔那丫头咋一回就蹦重点大学呢!那东西的命就比我强!”父亲的牙齿真脏,像黑炭。我给他递碗茶,他和着大颗大颗汗一口咕噜完。拐杖背依着土墙,悠闲地听知了吐舌头。
我其实是颗灾星。满月酒刚撤席,计生办的人就闯进来,中间杂着两个派出所穿制服的,人高马大,背着手瞪我父亲。父亲从灶窝抡一把菜刀要杀人,酒气撒狂起来,谁知背后飞来一脚,父亲栽到地上吃土,穿制服的踩着父亲的背,叫他动弹不得,其余踢翻二楼卧室门,抱走了电视,缝纫机,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直接给骑走了。戴帽的妇女一脸横肉,被我七岁的大姐绊了手,一巴掌就过来。母亲为我缩在床角,咬着嘴,听父亲千刀万剐的大骂不止。
踢我父亲的是他三弟,我三叔,爷爷疼他厉害,死前嘱咐要供他上学,他却入了一帮混混里做打手,被父亲几次拧着耳朵回来,却没改,兄弟从此结仇,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他替村长跑腿,是村里最“上进”的人。
“领官匪来抢的就是你畜生三叔!”母亲每次忆旧,都饶不过这道疤。反而父亲显得平静,每次提三叔,眼神如隔着三座山那么远。可村人都记得,父亲曾多么疯狂,暗暗惊悚。
那夜暗得快,家家门户早关,灯也歇得勤,山谷静得离奇。三更时分,村狗集体狂吠,嚎声震天,碎了几家胆怯的窗玻璃。三叔家养的狼犬也左冲又突卖着嗓子,越来越凶。三叔赶紧开灯探出窗帘子窥视。三叔个高壮,家距村长家近,又养条恶犬,谁敢招惹。可今晚似乎不同。
一团影子从暗处移出,慢慢挪近,三叔看得切,是我父亲。父亲肩一条石头,一手提着麻袋。村人知道要出事,各家男人举着火把渐渐靠拢来。
狼狗喷着鼻息准备扑咬父亲,父亲将麻袋一抛,漏出三五根白骨,恶犬突然收势,半晌,颠仆到麻袋前按住骨头猛啃,腿脚欢喜颤抖。父亲不由分说将石块砸去,烂了狗的腰,然后单腿跪地,用石块一响一响砸烂了狗的头,脚,身子,尾巴,血肉四溅,一片狼藉,父亲边砸狗边怒吼:
“你他妈的狗腿子,贱种,吃里扒外的畜生,你爹早死,养你到会放屁的是我!是我种地、砍木、轧钢筋供你读完小学,没良心没肺腑,我叫你吃,叫你吃你爹的骨头!”父亲号得像另一条疯狗,山鸣谷应,动荡不宁,嚎得人心千疮百孔。
父亲一身的泥土狗血,拨开众人回去了。三叔随后滚出门来,爬近一看,眼珠子直要掉:原来是爷爷的墓碑。
“爹,吃饭了。”我接着母亲的叫唤,一臂抱了父亲劈的柴禾,进屋扔灶室。回头见父亲扶着拐杖艰难挤进屋子。外头亮,里头暗,我看不清父亲脸,只觉得他像一副枯瘦的剪影。父亲真老了,老得见矮见瘦,老得让他有时忘记要强。上月大姐出嫁,亲戚直夸女婿能耐,这婚配得福气,父亲穿着喜庆人前也乐呵呵的。可有回我上厕所,撞见父亲呜呜在里头哭。
父亲瞅一眼桌上炒的热菜,努努鼻子嗅了嗅,“你娘整天搞他妈的招牌菜,也不怕我吃烦。”母亲舀一碗干饭过来,向我别嘴一笑。
“今年考得上么?”
“能!今年准考上。”
“这就对了!你就得给我长脸,也不费我给老乌龟拜了二十年香!”父亲说得动情,咬下一瓶啤酒盖,灌了半瓶,忽然把臂一伸,举我嘴边,“喝,咱爷俩干一回!”
我兴奋地捅了两口,咳嗽起来,父亲哈哈大笑,“咳嗽算个屁,继续喝,你爹我当年也咳嗽半死,除了你娘,谁来疼你?没人!人家巴不得看你糗,看你混蛋。儿子,你给我记好了,我和你娘早晚得死,”父亲顿了顿,“你得自个争气,苦干,肯把命赌上,别叫人看不起!”
我推开母亲劝来的手,一咬牙也开了瓶新的,这酒气呲呲往上鼓。酒真凉真冽,酒里藏了冰作的刀子,锋利,将我五脏六腑一寸寸割破,血撞着胸口,打着回旋。我一遍一遍咳嗽,差点没把肝肠吐出来,泪水哗啦啦,烫。父亲却只在那里笑,仰着脖子,往死里笑,他太开心了,他的龟儿子开始像他啦。
2012.11.25
|
|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
|闪小说作家论坛|手机版|触屏版|小黑屋|闪小说阅读网
( 闽ICP备2025097108号-2 )